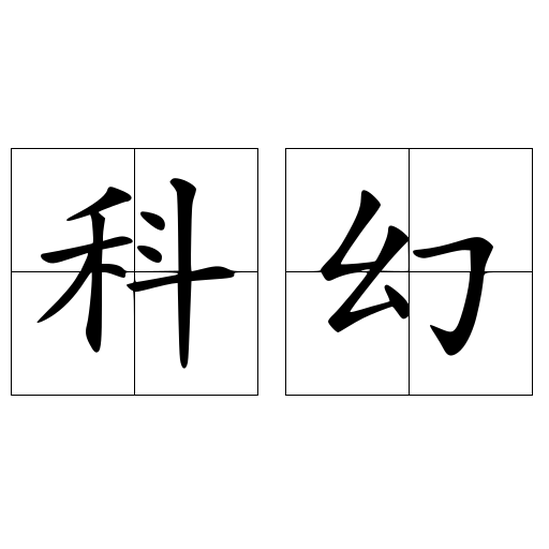傳統(tǒng)劃分方法
把科幻分為“軟科幻”與“硬科幻”,是科幻界內(nèi)部流傳最廣的一個(gè)分類法。而流傳得廣與劃分得合理。 具有理工背景的科幻作家,通常比較注重科學(xué)根據(jù),對(duì)科幻因素的描述與解釋也較為詳盡,令讀者不禁信以為真,這便是所謂硬科幻一派,而其中最硬的則非“機(jī)關(guān)布景派”莫屬(請(qǐng)注意“硬”在此并沒(méi)有“生硬”的涵義)。反之,一位科幻作家若是沒(méi)受過(guò)理工方面的訓(xùn)練,在描寫科技內(nèi)容時(shí)便會(huì)避重就輕,而盡量以故事情節(jié)、寓意與人物性格取勝,他們的作品自然而然屬于“軟科幻”。
疑問(wèn)馬上就出現(xiàn)了:難道“硬科幻”就不需要有好的故事情節(jié)、寓意與人物性格嗎?如果一部被劃分為“硬科幻”的作品在這幾方面上作得很出色,又應(yīng)該算是什么呢?相反,如果一個(gè)沒(méi)有受過(guò)理工方面訓(xùn)練的科幻作家并沒(méi)有“避重就輕”,反而刻苦鉆研科學(xué)知識(shí),最終寫出具有優(yōu)秀科學(xué)內(nèi)核的小說(shuō),難道又犯了什么禁忌嗎?比如凡爾納,就是被人們劃為硬科幻作家的宗師。他只不過(guò)是一個(gè)典型的文學(xué)青年,他的自然科學(xué)知識(shí)完全是自學(xué)的。所以,葉李華先生給出的定義是不能定性的。并且還明顯帶著對(duì)文科知識(shí)背景作者的岐視。 在大陸,早在七八十年代便出現(xiàn)了類似的分類:重視科技含量的科幻小說(shuō)是“硬科幻”,重視文學(xué)技巧的科幻小說(shuō)是“軟科幻”。當(dāng)時(shí),它們?cè)环Q作科幻小說(shuō)中的“重科學(xué)流派”和“重文學(xué)流派”。
凡此種種均經(jīng)不起推敲的。打個(gè)比方吧。一位廚師拿到一塊豬肉,他可以選擇紅燒、爆炒、清燉等作法。或者,他可以在紅燒豬肉、紅燒牛肉、紅燒魚之間作選擇。但他能夠在“紅燒”和“豬肉”之間選擇嗎?一個(gè)是原料,一個(gè)是烹飪方法,它們之間怎么能構(gòu)成兩極對(duì)立呢?科技是科幻小說(shuō)的主題、題材和素材,文筆是科幻小說(shuō)的技巧,這兩個(gè)東西分別是小說(shuō)的內(nèi)容和形式,怎么能分彼此呢? 將科幻小說(shuō)中的科學(xué)內(nèi)容與文學(xué)形式分開,到了九十年代又演變成將科幻小說(shuō)中的“科學(xué)成份”與“人性成份”分開,認(rèn)為主要寫科學(xué)知識(shí)的作品是“硬科幻”,主要寫人性的是“軟科幻”。這樣的定義更是危險(xiǎn)。它的立論基礎(chǔ)是:科學(xué)是反人性的東西,多一分科學(xué)便少一分人性,反之亦然。這種定義深入思考下去,會(huì)令人不寒而栗。因?yàn)樗鼘芽苹茫辽偈撬^的“硬科幻”排除在文藝圈之外。 還有一些人稱,根本不存在什么硬科幻與軟科幻,只存在“真科幻”和“偽科幻”。這兩個(gè)概念不見于正式發(fā)表的文字,但在網(wǎng)上交流或者私下聊天時(shí)經(jīng)常被提到。記得有一次,筆者遇到一位作者,問(wèn)他最近寫了什么作品。他的回答是,發(fā)表了一篇作品。但是不好意思,是偽科幻。
“真科幻”和“偽科幻”當(dāng)然也不是有理論意義的概念,只是意氣之爭(zhēng),是價(jià)值判斷而非真?zhèn)闻袛唷7Q一部作品是“偽科幻”,實(shí)際上等于說(shuō)它是冒牌科幻。
不過(guò),持這種觀點(diǎn)的人,如果和他們深入交流,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他們其實(shí)仍然是把那些習(xí)慣上稱為“軟科幻”的作品當(dāng)成“偽科幻”。把習(xí)慣上稱為“硬科幻”的作品視為“真科幻”,甚至是“純科幻”、“正統(tǒng)科幻”、“主流科幻”。他們放棄了“軟硬科幻”這對(duì)至少表面上貌似公允的概念,代之以更為偏頗的概念。
搞不清“軟、硬科幻”的定義,那么就看看被分別認(rèn)為是“軟、硬科幻”的那些作品吧。在《中華讀書報(bào)》上,一位北京籍科幻作家發(fā)表了《我所喜歡的十部科幻小說(shuō)》一文。他認(rèn)為,《2001太空漫游》是有史以來(lái)最優(yōu)秀的硬科幻作品。但這部作品怎么看,怎么是一部宣揚(yáng)宗教思想的神秘主義小說(shuō)。作者又稱,《一九八四》是有史以來(lái)最好的軟科幻作品,“當(dāng)1984年真正來(lái)臨之際,各國(guó)相關(guān)機(jī)構(gòu)開會(huì)研討,才發(fā)現(xiàn)書中130余項(xiàng)預(yù)言,有110多個(gè)均以實(shí)現(xiàn)。”(《中華讀書報(bào)》2002年九月25號(hào))那么,作了如此準(zhǔn)確之預(yù)言的科幻小說(shuō),傳統(tǒng)上不是應(yīng)該劃分為“硬科幻”嗎? 一九八一年,科普出版社出版了《論科學(xué)幻想小說(shuō)》一書。筆者在這本書中找到這樣一段論述:“史密斯(一位八十年代初到上海講授英語(yǔ),并將科幻小說(shuō)作為鋪助讀物的美國(guó)人)還給我們介紹了一種關(guān)于科學(xué)幻想的新概念。在美國(guó),人們把科學(xué)幻想分為”硬幻想“與“軟幻想”。“硬幻想”是指幻想以物理、化學(xué)、生物學(xué)、天文學(xué)這些自然科學(xué)為基礎(chǔ)的,是“堅(jiān)硬”的科學(xué);“軟幻想”則是指幻想以社會(huì)學(xué)、歷史學(xué)、哲學(xué)以及心理學(xué)等“柔軟”的科學(xué)為基礎(chǔ)的。這與中國(guó)的關(guān)于以“文”為主,以“科”為主的科學(xué)幻想小說(shuō)的提法,是不同的概念。(摘自《論科學(xué)幻想小說(shuō)》235頁(yè),《太平洋彼岸的科學(xué)幻想熱潮》,葉永烈撰) 當(dāng)然,不能因?yàn)檫@個(gè)定義是美國(guó)人下的,就想當(dāng)然地認(rèn)為比中國(guó)人下的定義正確。但這是筆者找到的,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分類法了。因?yàn)樽匀豢茖W(xué)和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區(qū)別就擺在那里。根據(jù)這個(gè)定義,我們可以認(rèn)為,寫遺傳工程、太空探險(xiǎn)題材的是硬科幻,寫人口問(wèn)題、社會(huì)學(xué)問(wèn)題的是軟科幻,等等。至少,這個(gè)定義沒(méi)有把“生煎”和“牛排”兩者對(duì)立起來(lái),他們考慮的是煎牛排還是煎豬排的問(wèn)題。 不過(guò),這樣給“軟——硬科幻”下定義,理論上雖然沒(méi)問(wèn)題,實(shí)踐中仍然有極大缺陷。因?yàn)橐陨鐣?huì)科學(xué)為題材的科幻作品,數(shù)量和影響力上遠(yuǎn)遠(yuǎn)小于以自然科學(xué)為題材的作品,連后者的零頭都不到,怎么能夠成為兩大基本類型之一呢?甚至,科幻小說(shuō)習(xí)慣上只被認(rèn)為是描寫自然科學(xué)題材的。筆者猜測(cè),即使是歐美科幻界,恐怕也不是在這個(gè)意義上使用“軟硬科幻”的概念吧。
“可以劃分出‘認(rèn)知’和‘審美’兩種意義上的科幻小說(shuō),前者的代表人物應(yīng)當(dāng)是阿西莫夫,布拉德伯雷、克拉克則是后者的典范。”(嚴(yán)蓬《關(guān)于鄭文光科幻小說(shuō)的審美分析》轉(zhuǎn)引自《鄭文光70壽辰暨從事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59周年》)這是對(duì)“軟硬科幻”概念的某種提升。不過(guò),科幻本身,甚至任何敘事類文學(xué)作品本身,都是“認(rèn)知”和“審美”的綜合體。將兩個(gè)不能分開的部分分開是不成立的。 “軟硬科幻”雖然不是一對(duì)有理論價(jià)值的概念,但它們反映了科幻界內(nèi)部,科學(xué)與人文兩種文化傾向的沖突。不過(guò),那不是在本章中討論的問(wèn)題。
除了“硬科幻”“軟科幻”這對(duì)流行概念外,還有一些科幻作家從其它角度對(duì)科幻文學(xué)進(jìn)行過(guò)劃分的嘗試。比如以下兩個(gè)論點(diǎn):
“科幻小說(shuō)大體可以分兩種:一種是走通俗路線,娛樂(lè)的;另一種比較有哲學(xué)意味,”(鄭文豪《臺(tái)灣科幻小說(shuō)精選》451頁(yè))這個(gè)分類采用了“藝術(shù)——通俗”的兩極分類法。在下面“科幻文學(xué)與通俗文學(xué)”的關(guān)系里,筆者要討論相關(guān)的內(nèi)容。
“一,探險(xiǎn)科幻小說(shuō):敘述人在時(shí)間空間中的各項(xiàng)探險(xiǎn)故事。
二,機(jī)關(guān)科幻小說(shuō):敘述新奇的科技發(fā)明對(duì)人類可能帶來(lái)的影響,如機(jī)器人、飛碟、死光槍、愛情機(jī)器等。
三,社會(huì)科幻小說(shuō):預(yù)測(cè)人類社會(huì)未來(lái)的可能發(fā)展,也諷刺社會(huì)不合理現(xiàn)象,如《一九八四》、《美麗的新世界》等。
四,幻想小說(shuō),以幻想為主,科學(xué)的成份減少或完全沒(méi)有,包括三種,烏托邦科幻小說(shuō)、鴛鴦科幻小說(shuō)、文藝科幻小說(shuō)。”《臺(tái)灣科幻小說(shuō)大全》503頁(yè)。這個(gè)分類的標(biāo)準(zhǔn)是很模糊的。僅作為資料收錄在此。 在《科幻的分類》(《科幻世界》96、4)一文中,吳定柏先生介紹了國(guó)外研究者在這個(gè)問(wèn)題上的一些結(jié)論。比如,有的將科幻作品從外在形式上分為“趣味性作品、預(yù)言性作品、社會(huì)評(píng)論性作品”;有的從主題思想上將其劃分為“樂(lè)觀主義和悲觀主義”兩類;有的依照題材不同將其劃分為“技術(shù)、人類利益、社會(huì)學(xué)和末世學(xué)”四類;有的則直接根據(jù)科幻構(gòu)思所屬的科學(xué)門類進(jìn)行劃分。 前蘇聯(lián)科幻作家在研究西方的科幻小說(shuō)時(shí),認(rèn)為西方的科幻作品敢于想象幾百幾千年后的未來(lái),而當(dāng)時(shí)的蘇聯(lián)科幻顯然沒(méi)有這么“遠(yuǎn)”。于是便有遠(yuǎn)科幻、近科幻的奇怪分類。當(dāng)然,那些蘇聯(lián)科幻作家并非要把這對(duì)概念變成一對(duì)基本概念,只是用它們來(lái)描述自己的某種觀感。但科幻中的幻想之分遠(yuǎn)近,確實(shí)是一個(gè)有趣的現(xiàn)象。
總得來(lái)說(shuō),與科幻文學(xué)已經(jīng)積累得很豐富的文本相比,對(duì)其分類進(jìn)行的理論探索是遠(yuǎn)遠(yuǎn)不夠的。
被種種分類搞得頭疼的某些科幻作家,干脆就反對(duì)一切分類。他們認(rèn)為,科幻作品只分好壞,有人讀的科幻就是好科幻,沒(méi)人讀的就是次科幻。這么分就行了。這樣就避免了無(wú)休止的,看似也無(wú)意義的爭(zhēng)論。
其實(shí),搞清科幻小說(shuō)的內(nèi)部門類在實(shí)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如前所述,科幻文藝本身就是從大文藝中分化出來(lái)的一個(gè)類型文藝。科幻在成熟過(guò)程中,內(nèi)部又不停地分化。這個(gè)過(guò)程其實(shí)就是讀者細(xì)分的過(guò)程,也是作者分化的過(guò)程。擅長(zhǎng)寫這類科幻的作者不擅長(zhǎng)寫那類科幻;喜歡看這類科幻的讀者不喜歡看那類科幻。對(duì)于作者來(lái)說(shuō),哪些讀者是自己的目標(biāo)讀者?對(duì)于出版社、雜志社來(lái)說(shuō),哪些讀者是自己的消費(fèi)群體。他們絕不能不考慮這個(gè)問(wèn)題。
這其實(shí)是一個(gè)要不要分灶吃飯的問(wèn)題。科幻的家業(yè)大了,以前混在一起的幾個(gè)兒女,要不要分開另過(guò)呢?如果考查一下對(duì)于某部科幻作品的批評(píng)意見,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其中有很多都是沒(méi)有分家?guī)?lái)的后果:持這些批評(píng)意見的讀者,根本不是這類科幻作品的讀者。但他們認(rèn)為,科幻應(yīng)該是鐵板一塊,只有自己那一類才是正宗。而被他們批評(píng)的作品恰好不屬于這個(gè)“正宗”。
從邏輯學(xué)的角度講,要進(jìn)行劃分必須先確定劃分的依據(jù)。總的來(lái)說(shuō),以上那些劃分工作在確定依據(jù)方面作得都不夠深入和清晰,導(dǎo)致分類的結(jié)果也含糊不清。筆者的分類標(biāo)準(zhǔn),是一個(gè)敘事學(xué)的標(biāo)準(zhǔn):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。 (小說(shuō))敘述的事件不僅有上述邏輯上的關(guān)聯(lián),也存在著等級(jí)的區(qū)分,即不僅有橫向的、水平的聯(lián)系,也有縱向的、垂直的區(qū)分。在敘述的事件中,一些事件顯然比另外一些更重要,即一些是主要事件,一些是次要事件……前者是敘事闡釋語(yǔ)碼的重要部分,它通過(guò)提出問(wèn)題和回答問(wèn)題來(lái)推進(jìn)情節(jié)……而“次要”的事件在這種意義上卻沒(méi)有這樣重要,即使省略也不會(huì)影響整個(gè)情節(jié)的邏輯,盡管這種省略會(huì)給小說(shuō)的審美價(jià)值造成損害……它們的任務(wù)是豐富、具體和完成中心事件。
劃分作品,首先要挑出它的主要事件。具體到科幻而言,科學(xué)是科幻的源文化。對(duì)于不同的科幻作品來(lái)說(shuō),它的主要事件和客觀的科學(xué)技術(shù)知識(shí)之間有什么樣的聯(lián)系,是筆者進(jìn)行分類的基本標(biāo)準(zhǔn)。以此為據(jù)。認(rèn)為科幻小說(shuō)至少劃分為以下六大門類:預(yù)言類科幻、創(chuàng)意類科幻、象征類科幻、傳奇類科幻、反科幻和元科幻。